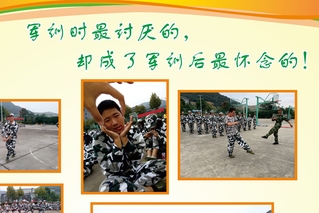开放教育学院教师 周晴
我曾是贝塔斯曼中国书友会的会员,所谓的会员待遇,就是每个月书友会会邮来一份推荐购书目录,目录上会有当月优惠打折的精品书籍推荐。其实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加入该书友会的——可能是莫名其妙地在一些传单上填写了个人信息吧,但既然已经成为了会员,总还是会定期购买一些书籍,既显得自己很有文化,又觉得占了打折买书的便宜。
1998年,我在书友会邮来的目录上看到了一部书,名字是《地久天长——王小波小说剧本集》。这本书的边上写着推荐评语,大体是:王小波以其优秀的杂文著称,其实他的小说也很精彩,特别是书中的《东宫•西宫》是一部涉及同性恋题材的剧本,还获得了阿根廷马塔布拉塔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剧本奖。
当时我并不知道王小波是什么人,也不清楚这个阿根廷的国际电影节算是个什么水准,但是处于少年人对于同性恋题材的好奇,我还是购买了这套书。几天后,书到了,首先看的当然是那部《东宫•西宫》,看了之后懵懵懂懂:几处简单的场景——公园、派出所;两个重复对话的人物——阿兰和警察小史;几个晦暗生涩的动作——抱头、下蹲、闭目、靠墙。气氛压抑,欲言又止的状态让人觉得心里有说不出的沉闷,好像有无边的黑暗将人压得透不过气。
只对其中的一段台词印象深刻:
“这不重要,当你想爱的时候,你就是男的。当你想要承受爱的时候,你就是女的。没有比这更不重要的事情了。我为什么要是男人或是女人?我可以是你喜欢的任何人,也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。你可以践踏我的一切,只要你允许我爱你。”
这段台词,在当时看来骇人听闻,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冲击。我头一次模糊地意识到,对于青春末期的少年来说,在他们假装走向成熟而事实上仍然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阶段里,很多事情并不该像你所认为那样是茫然、怅惘的,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活着的主题,就比如追求爱情的人,他的生活主题就是爱情,无关男女。这是近乎直白的生命诉求。
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记得那段台词。但是这个剧本,或者电影,却是意有所指的——当时某城市以所谓健康调查的名义,清查了一些同性恋群体。后来我看到了这部电影的导演张元的一段话:“这简直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令人发指的暴行。”当然,这些都是后话。
1997年,王小波在家中心脏病突发辞世,享年45岁。此前,他并非知名作家,而他死后,作品开始广为人知,就在去世的那个月,《东宫西宫》在阿根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编剧奖;同年,电影《东宫西宫》入围戛纳电影节。历史如此诡异,他生前的寂寞与身后的盛名形成了巨大反差。
这一切对于当时的我来说,都不重要,如前所述,我只是一个处在青春末期的少年。在陆续看完了他《地久天长》里的其他作品后,我开始看他的代表作《黄金时代》。
那时我正在上大学,寝室里电脑尚未普及,夏夜里,一群光着膀子、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每天和蚊子做着艰苦斗争。晚上熄灯后,这些精力充沛的人总是不会马上入睡,有人拿出了应急灯,我便躺在蚊帐中开始看书。
“陈清扬说她真实的罪孽,是指在清平山上。那时她被架在我的肩上,穿着紧裹住双腿的筒裙,头发低垂下去,直到我的腰际。天上白云匆匆,深山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我刚在她屁股上打了两下,打得非常之重,火烧火撩的感觉正在飘散。打过之后我就不管别的事,继续往山上攀登。陈清扬说,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,就瘫软下来,挂在我肩上。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,小鸟依人,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,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全部遗忘。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,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。”
夏夜的男生寝室里总是充满一股酸臭味,《黄金时代》里的经典文字在这股酸臭味中读起来,让人觉得格外伤感。看着看着,身边就有一个脑袋挤了过来,伴随着一阵怪腔怪调的话语:
“兄弟!你在看啥呢!……(过了一阵)哟!这不是黄书嘛!”
我哈哈大笑:“是啊,看完了借你。”
《黄金时代》所受到的诟病,就是对某些场面的描写过于露骨。其实,就王小波自己说来,这本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,反而他更尊重女性,如同陈清扬,有勇气、有担当,引领王二走过了那最艰难的一段,她是灵魂之火,生命之光,即便有很多粗口和脏话。
《黄金时代》的写作背景定位于文革时代,小说里的男主人公王二以浑浑噩噩的状态挑战着既有秩序,因为他觉得周遭的一切过于“不正常”,于是刻意摆出一副混不吝的样子。当他遇到了陈清扬,这两个在别人看来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人,反而一起用自己的抗争方式证明了世人的可笑。说实话,在我看《黄金时代》的时候,觉得书里的情景有点眼熟——我看了看周遭的光膀子青年们,有的在和女友打电话,有的闭着眼睛带着耳机听摇滚乐,有的鼾声震天,有的捧着块西瓜一边大啃一边和人聊天,包括我自己,也是每天无所事事不知所云,这像极了那个游手好闲的王二。要补充的是,每个青年大学生都是对大学生活有憧憬和畅想的,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有的人会对周围的青年女性产生无限倾慕。几年的大学生活里,每当我看到那段话的时候,都会产生一股冲动:不管她同意不同意,抱上她横架在肩上,一往无前的冲过去,直到天涯海角。可惜的是,我们遇不到陈清扬,我们看不懂自己的黄金时代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这股冲动也就慢慢没有了。
但是《黄金时代》还是让我看到了说真话的魅力,长久以来说真话已经成为了一种奢侈,如果说现代汉语文学还存在一定魅力的话,那么以《黄金时代》为代表的小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。透过这扇窗,我看到了一些新鲜事物,开始了解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。其实我们一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,但是就是看不清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。在《黄金时代》的后记里,作者写道,20世纪初,有一位印象派画家画了一批伦敦的风景画,在伦敦展开,引起了很大轰动——他画的天空完全是红的。观众当然以为是画家存心要标新立异,然而当他们步出画廊,抬头看天时,发现因为污染的缘故,伦敦的天空的确是砖红色的。王小波说,天空应该是蓝色的,但实际上是红色的。正如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他写的那样样,但实际上,它又正是自己写的这个样子。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——我们所看到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,我们所做的也并一定是正确或“正常”的。
之后又陆陆续续看了王小波的《革命时期的爱情》、《我的阴阳两界》、《红拂夜奔》,还有他的一些著名杂文,《我的精神家园》、《我为什么写作》、《我的师承》等等,王小波的文字几乎涵盖了我的整个大学生涯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文字始终体现了一股浓厚的自由主义精神,李银河曾在怀念王小波的文章里称王小波一个浪漫的骑士,自由的行吟诗人,他自由的思考,凭本心而活,以客观、冷静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,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美好,就如王二追求陈清扬,直白、热烈,不理会世俗的眼光,坚守自己内心的纯粹。说到这里,令人不由得想起王小波给李银河写过的情书:“银河,你好!做梦也想不到我把信写到五线谱上吧?五线谱是偶然得来的,你也是偶然的来的。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。但愿我和你,是一直唱不完的歌。”——你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可爱的人,比这更美好的感情了。
几年前,我坐火车去外地,因为车程时间很长,怕路上无聊,就想带本书在车上,在书柜里翻了半天,最终还是带了本《王小波文存》。
路上,我打开书,漫不经心地翻看,突然有一句话映入眼帘:“似水流年才是一个人的一切,其余的全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。”
在历史长河里,只有时间才是永恒的,其他一切都是插曲。当时年少,读书遣怀,或有欢娱,偶有伤怀,未曾想到如今的种种周转,那个贝塔斯曼中国书友会已经在2008年关闭,还有那个曾经我想扛着去天涯海角的“陈清扬”,也已经拜拜了。